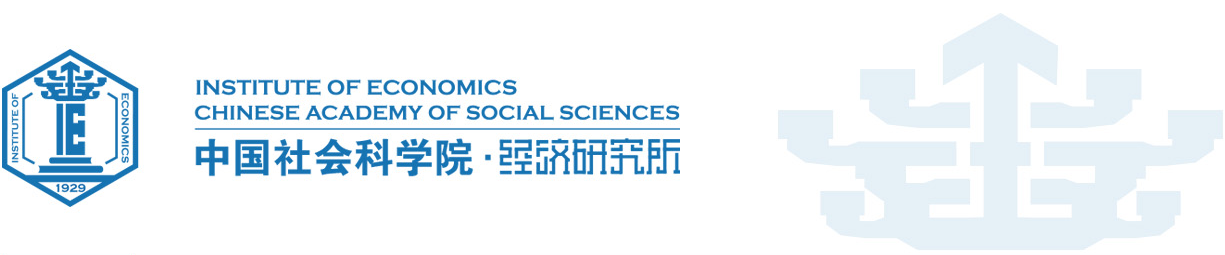作者:王砚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馆长)
来源:《经济学家茶座》第87辑
图书馆人一直以来绝大多数都是默默无闻的,很少有一位图书馆人能在图书馆学界以外的领域为人所知。但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曾有一位老先生,他的名字至少在经济学人中耳熟能详。这位先生,就是将一生都奉献给了经济所的宗井滔。

约为20世纪60年代,宗井滔先生和经济所图书馆同事们合影。左一:刘琢玉、左二:张志元、中:宗井滔;右二:张泽厚、右一:刘国贤(张志元遗藏)
宗井滔先生在学界广为人知,要归功于吴敬琏先生,在1997年第4期《百年潮》接受邢小群采访的《我与顾准的交往》中,吴敬琏先生回忆说,“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在馆长宗井滔的主持下,继续订阅国外期刊杂志,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美国经济评论》一类西方学术刊物。”此后柳红《吴敬琏评传》、吴晓波《吴敬琏传》等著作也转述了这段回忆。而徐方的《干校札记》则讲得更详细,据她叙述,顾准最后两年读的书当中,“经济学文献则大部分来自经济所图书馆”。“一次,顾伯伯从宗井滔先生那里拿来一本美国经济学会的高级学术刊物:《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从中选出几篇最新的探索性经济学论文,分给吴敬琏叔叔、赵人伟叔叔和我母亲(注:经济所学者张纯音),让他们拿去翻译,翻好之后由他来批改。”
宗先生在学界相传的事迹,主要就是以上见载于文字的这一部分。但其实,宗先生对于经济所来说,是当之无愧的元老,一生服务了几代经济所学者,在学人中赢得了崇高的声望,堪称经济所和图书馆的“守护人”。宗先生1933年就进入经济所的前身机构,当时的社会调查所担任“临时计算员”,历经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经济研究所,直到1987年底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退休,在经济所及其前身机构工作了整整55年,几近一个甲子,除他以外,资历如此深且能在经济所“从一而终”的只有同年被社会调查所选为研究生的巫宝三先生。
我到经济所图书馆工作不久,就从同事的口中知道了宗先生,在经济所图书馆,宗先生是神一般的存在,大家提到他的时候都尊称他“宗先生”“宗老”。我在工作中翻检藏书的时候,不时会发现一些卡片,记录着藏书采购来源、版本考证等等,那些字迹很不好认,看得多了才逐渐能认出大概的意思。其中夹在一部雍正《大清会典》中的卡片上记录着:1938年,此书在辗转途中,于广西河池遭日机轰炸,虽经全力抢救,但前九卷仍遭焚毁!后来慢慢看得多了,我才知道,这些记录,都出自宗先生之手。
宗井滔先生,原名宗抡元、字尔菼,1909年10月9日出生于当时的察哈尔怀安,初三未读完因参加政治活动被学校开除,自此失学,此后辗转河北、北平等地,动荡中求生,曾在北京大学等机构从事文书等工作,1933年7月考取了社会调查所的“暑期临时计算员”,从事抄写、计算工作,负责进出口贸易值量统计,9月因“成绩优良”正式留任“计算员”。“井滔”的名字是宗先生从1933年报考社会调查所的时候开始使用的。
宗先生加入社会调查所后,还有一个小插曲:1933年9月下旬到10月下旬,宗先生被无由指认遭北平公安局逮捕拘禁一个月后又无由释出,社会调查所期间曾由秘书林颂河设法营救,其后也并未追究,继续请其任职,并建议他由北大工学院宿舍迁至社会调查所在酒醋局胡同的宿舍。此后,无论机构名称如何更改,所址如何变迁,宗先生再未离开。
宗先生深得陶孟和所长的信任和重视,他长期担任社会调查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事务员、文书员,代陶孟和先生起草了大量的文件,1938年起兼管图书,1942年3月,正式被任命为图书管理员,仍然兼管文书,1947年7月起专管图书。从1934年起,直到陶先生离开研究所之前,在履历表中,宗先生在“证明人”一栏填写的都是“陶孟和”,由此可见陶孟和先生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1937年抗战爆发后,社会科学所向西南转移,宗先生和一些同事负责将图书、设备等物资乘船乘车辗转长沙、衡阳、桂林、昆明、李庄,1946年9月迁回南京。抗战期间,很多研究所的人员都先后离去,宗先生则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岗位,并在李庄结婚生子,抗战结束后,1946年,宗先生获国民政府“胜利奖章”嘉奖。
宗先生在所里,开始从事的是行政工作,但他一直在学习,巫宝三先生说,“他爱好书刊并勤学外语(不止一种),所以到抗战时当原图书管理人员离任后,他就既是文书又是图书管理员,而他勤勤恳恳,朝夕如是,把所内图书摸得一清二楚。”同事评价他“记忆力好,自修能力强,所以社会所的图书馆由他管理(他没有正式学过),他非常熟悉,离不开他,做事很仔细而负责任。”
通过自学,他掌握了英、德、法、日、俄等多门外语,而且他对学者及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了如指掌,由此就能很有针对性地采集相关的书刊文献。作家王晓林在评价宗先生时说到,他不但“熟悉图书,也熟悉需要这些图书的人,不但熟悉这些人,还知道他们的研究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总而言之,他了解学术的发展方向和历史的延续过程,提前就为研究人员准备好”。而这是宗先生最为难能可贵也是给人印象深刻的一点。
宗先生如此熟悉学者的需要,是付出了我们无法想象的辛劳的。2018年底,我采访了1953年来到经济所图书馆工作的汪熙曾老人。她回忆到:她刚到经济所图书馆时,宗老先生已经全部掌握了图书馆采购分类编目的整个工作。在中关村的时候,采购书都要进城,宗先生每次搞得五六点钟下班以后才回来,背了一大堆书。回来以后,他还不下班,还要看书,从来没有上班下班的观念,经常六七点钟才回家。宗先生对馆藏很熟悉。像严老(注:严中平)他们,从来不查目录,直接问老宗,他马上就能找出来。
宗先生为经济所的馆藏建设可谓是殚精竭虑。宗先生的长子宗丕钊在“经济所90年发展回顾和未来展望”主题论坛上回忆,“在父亲的枕边,总是堆放着国内最新出版的中外经济学类图书资料订购期刊目录,对需要购进的图书、杂志都做上记号。”朱荫贵研究员也回忆说,宗先生不仅是活字典,而且他在经济所的21年里,关于经济史的资料,很多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其他的地方完全找不到的资料都是在经济所图书馆找到的,如晚清汉冶萍煤铁有限公司第1至第8届账略的资料书,还有记录抗战时期上海地区股票买卖三年多的《华股日报》等等等等,关于民国证券市场的宝贵资料,甚至成为直接促使他对中国近代证券市场研究产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
宗先生除了为经济所图书馆采购了大量珍贵的专业文献资料,还在经济学文献的分类编目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他曾与人合著《经济、经济科学图书分类法的基本类目及序列问题》一文,1959年参加了北京图书馆组织的大型《图书分类》经济学类目的草拟工作。中国科学院著名图书馆分类学专家白国应曾撰文说,在编写《科图法》时,他专门向宗先生请教关于经济学文献分类的问题。另据经济所图书馆老馆长刘厚成回忆,宗先生把图书馆的珍贵印本、稿抄本、抄档等都做了卡片档案,馆里后来据此整理编印了一册经济所图书馆特藏目录。

宗井滔先生给我们留下的书刊登记本中的一页
图书馆现在留存的一批档案中,有宗先生的一个记事本,里面详细记录了图书馆历年的采购和入藏种类、数量和价值,将图书馆的藏书资产梳理的清清楚楚。在1964-1968,1973-1975年期间向外文书店、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订购的外文报刊统计中,“资版”(即当时对欧美原版书刊的称谓)报刊的数量,1964年到1966年超过100种,1967年是78种,1968年是67种,而且其中记录的1964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各研究所外汇额度中,经济所的经费是最多的。在另一份统计中,从1966年底到1968年底,图书馆各类书刊均有新增,这3年中,其中西文书总计新增837册,西文刊新增746册。此后的1969年到1970年,也就是下放河南干校期间,新增报刊基本是空缺的,到1971年,又开始有新书到馆记录。到1972年以后,新购书刊数量则大幅增加。汪熙曾老人在回忆那段时期时说:宗先生不参加运动,就只做他手里的工作。外文书刊都是他在管,因为别人管不了,没人能接手的。
按宗先生的年龄,到1969年他已年满60岁,但一直也没有退休。1969年11月,宗先生曾随经济所下放到河南息县,1970年5月因经济所由经委大楼搬迁至建国门学部大院集中,调回北京留守,直到1971年学部返回北京。学部返回北京后,各项工作才开始逐渐恢复。从那段历史背景和宗先生的记录数据来看,大概只有这段时间,宗先生无法正常地采购新书刊。宗丕钊还叙述过一段往事,他说“记得有一次父亲情绪激动地说要写申述材料,原因是要取消一种期刊的订阅,父亲强烈反对,因而要向上申明订阅的理由。”根据宗先生详细的统计记录,以及他维护学术期刊订购的坚决态度,基本可以印证了吴敬琏先生等人关于宗先生在“文革”期间坚持订购外文图书期刊的回忆。
“文革”时期,还有一段堪称“惊心动魄”的历史。老所长孙冶方曾叙述:在学部撤到河南干校待命分配的那段时期,在经济所掀起了烧书卖书高潮,经济所的几十万册珍贵藏书,也准备全部送人。“要不是一方面当时没有机关肯接管这么多的藏书,另一方面我们的图书馆负责人、宗井滔等同志事业心重,……坚持接收机关不能零星挑选,而要全部藏书一起移交”,这批馆藏早就损失掉了。汪熙曾老人也回忆说,在“文革”期间图书馆没有大乱,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宗先生起了很大作用。可想而知,假如当时的倒行逆施不幸成真,那么现在的经济所图书馆早就面目全非了。
宗先生一生乐为他人做嫁衣,如今在经济学研究领域能够查到的著作只有在1942年第3卷第1期《中农月刊》发表的译作《伪满的农业专卖统制》(John R. Stewart原作),和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与汪敬虞、聂宝璋、张国辉等合译,署名“敖文初”的经济研究所译丛第二种:《封建农奴制时期俄国的商人资本》(雅可柴夫斯基原作)。另外,从宗先生的手稿中大致可以推断出,1948年出版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1928-1948)》一书中社会所的概况和成果目录,应该也是由他编写的。
汪熙曾老人在访谈时肯定地表示,经济所图书馆的基础是宗先生打下的,图书馆很多人能够坚持这个事业,也是与他的指导和帮助分不开的,很多人都是他带出来的徒弟。

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之间,宗井滔先生(后排左二)和经济所图书馆同志在三里河办公楼前合影(张志元遗藏)
宗先生曾写下过这样的个人志愿:愿以图书馆工作作为终身事业。从他的一生经历来看,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图书馆的事业,他确实做到了言行合一。
1982年底,中国社科院恢复评定职称工作,1983年的第一届院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经济研究所吴敬琏、田光为研究员,宗井滔为研究馆员。宗先生成为了社科院恢复职称评定后经济所第一批晋升正高级职称的专业人员。1992年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学者、技术人员名录》,宗先生也赫然名列其中。
经济所研究员、经济所图书馆顾问封越健认为,宗井滔先生是值得我们大写特写的。一所优秀的研究所,必须有优秀的图书馆,而优秀的图书馆必定有优秀的图书馆人,宗井滔就是优秀图书馆人的杰出代表。我们总结宗先生的贡献,认为他一是通过长期积累建设起了经济所“专、深、特、精”的特色优势馆藏,这是建立在他通晓多国文字、有学术研究能力,熟知研究所的学科建设方向、研究项目、学者需求和偏好、馆藏情况、资源渠道基础之上的;二是为科研人员提供极其优秀的服务,在科研人员中有口皆碑,交口称赞,这是建立在他守护学术、全情投入、服务至上理念基础上的。而宗先生的做法和理念,代代传承,成为经济所图书馆的重要特质。
为了写宗先生,我查阅了档案,其实,宗先生从来没有被正式任命为图书馆馆长,但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宗先生绝对是经济所图书馆人的代表、灵魂和标杆,是经济所和图书馆的“守护人”。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第87辑,部分内容有修改。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刘凤英、封越健,黄晨等同仁的热情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编稿:张佶烨;审校:王砚峰)